“传统+创新”,上海中药涅槃归来!
时讯

生产“六神丸”的“雷允上”是上海知名的百年老字号,与“童涵春堂”、“胡庆余堂”、“蔡同德堂”并称为本土四大中药招牌。上世纪中下期曾是海派中药的鼎盛时期,转制而成的上海中药一厂承古融今,创造了中成药市场上的诸多第一。
72岁应杨生是上海中药厂的退休员工,40多年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上海中药的大起大落。最鼎盛的时候,老应几乎天天泡在厂里,没有一刻得闲,生产车间24小时高速运转。“新鲜出炉”的中成药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送,即便如此,一些明星产品还是“一抢而空”。

“像我们生产的六神丸都要领导批条子才能买的,麝香保心丸也是要批条子的,看你面子才买给你的。”
然而,中成药的良好涨势却在90年代急转直下。
1994年,国家颁布了《药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药品须按统一的招标价对外出售。对于那些不惜成本,“精雕细琢”的中成药来说,这无疑是一记晴空霹雳。

产自上海的南派阿胶便是在这轮冲击下被迫停产。
应杨生至今仍珍藏着药厂生产的最后一批驴皮胶,上海是南派阿胶的传承方,这是一种选材考究、制作精良的本土工艺,对原材料、水都有严格要求。据说100公斤的驴皮只能生产30公斤的阿胶。1995年,南派阿胶停产。
“当时的驴皮胶单价只有十几块钱,但是当时生产这些驴皮胶的原材料成本就要十几块钱,你说怎么坚持得下去”,说起这段历史,曾为上海驴皮胶厂厂长的老应颇显无奈,“到现在我都只认我们上海的阿胶最好。没有了,再也没有上海阿胶了。”

除了成本限制之外,原材料短缺、来自西方医学的冲击等原因也制约着本土中药的发展。
再比如麝香是六神丸中一味必要成分,在当时,天然麝香极其难觅,而人工麝香又没有研制出来,传统名药不得不在停产的边缘苦苦挣扎。
停产的停产,萎缩的萎缩,入不敷出者比比皆是,即便是一些“活”下来的药企和中成药品类,也不得不通过降低成本、简化工艺的办法苦苦支撑,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源头的失控,重金属超标频频发生,因为中药原材料多为散户种养,而后由药企统一购入,也就是说,企业并不参与到原材料的生产环节中去,原材料质量如何全靠小农的自觉性,但情况并不乐观,拿业内人士的话来说,中成药的种养殖,远远落后于中国农业的水平。

另一个令中药悲哀的现实是,来自“洋中药”的冲击。
数据显示,在国际市场上,“洋中药”的市场份额早已远超中国。国人出国海淘,都不忘带上两盒“汉方制剂”回家。就连去年令国人引以为傲的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女士发现的青蒿素,也被他国抢先注册。
自己的“孩子”,为什么给比人“抢”了去?还要这样低迷下去吗?

2015年,国家开始放开药物定价的“紧箍咒”,今年初,国务院又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提出扎实推进中医药继承和创新。在上海中药行业协会副会长陈军力看来,这针“强心剂”让复苏本土中药看到了希望。
“保证原材料的质量,以高出国家标准的制药技艺生产,才是出路。”
借着这波东风,曾经让老应抱憾不止的南派阿胶开始了漫长的“重生之路”。
新疆喀什是全国最大的毛驴产地,纯净的水源、无污染的湿地是生物最理想的栖息场所。近期,停产了20年的上海南派阿胶就在这里重新投入生产。

除了纯天然的生长环境,每头毛驴都必须追根溯源,它的母亲是谁?父亲是谁?每头毛驴都会进行芯片跟踪,跟踪内容细致到毛驴每天的食物。
而传统的老上海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相结合也体现在了后期的生产环节中:驴皮必须两面都清理干净,熬制过滤环节虽有机器辅助,也必须保证每40分钟一次的人工去渣,机器功率再大,也必须细火慢熬,待48小时之后才开始风干。再经过至少一周的时间,定型切割,成品才初现雏形。
不久的将来,这一块块深含“上海基因”的阿胶就将重新投放市场。事实上,因为中成药必须严格依据《药典》来生产,所以这些成品并非还原了真正意义上的南派阿胶,比如南派阿胶经典的“油头”就无法体现在最终的成品中,但至少,这已经为老技艺及背后文化价值的传承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方面是经典再现,另一方面,传统的老品牌也在谋求自身的创新和发展。比如研究表明,“六神丸”对传统病症以外的一些疾病治疗具有奇效,雷允上表示,他们将不断加大科研力度,让这一味“百年名药”发挥更广阔的药用价值。
推荐视频

剑网行动举报电话:12318(市文化执法总队)、021-64334547(市版权局)
Copyright © 2016 Kankanews.co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看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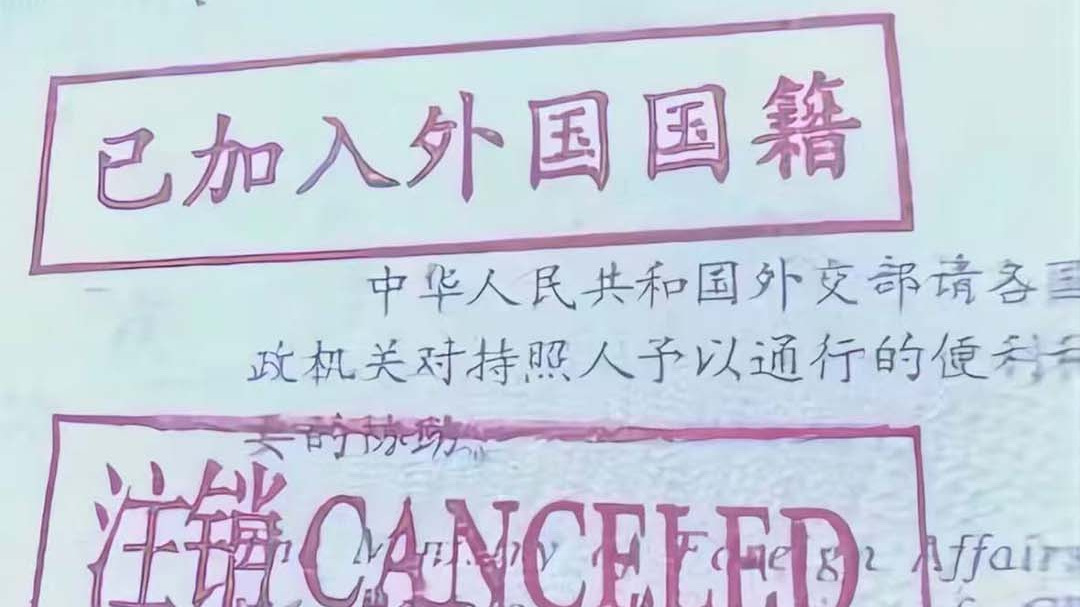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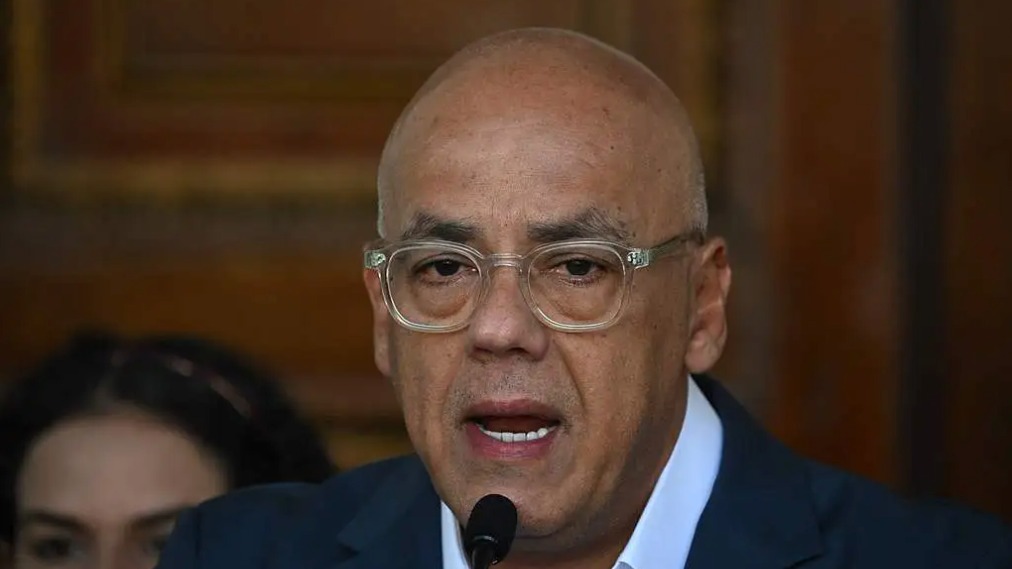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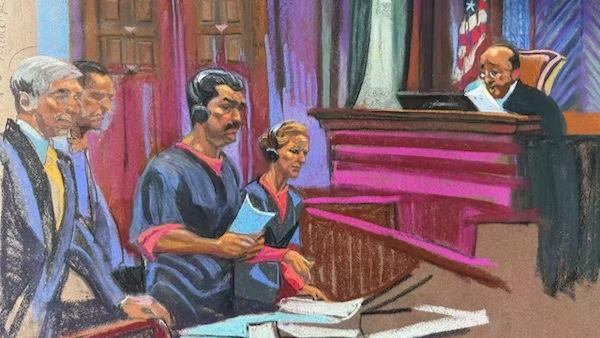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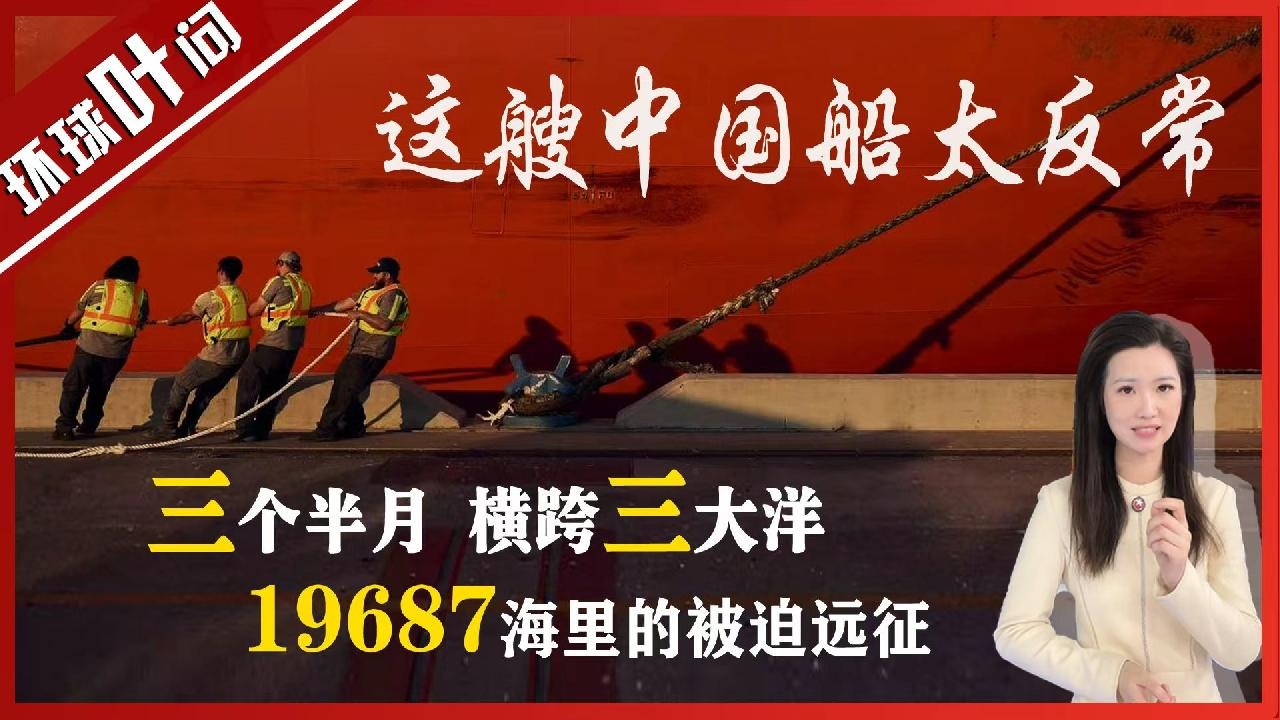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11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11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