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乡村遇上互联网(中)
时讯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也有过深重的乡村危机。一批进步的社会学者、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民间团体为了解决当时农村严重衰败的局面,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它以社会实践为基本路径,在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知识分子的倡导与身体力行中,曾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
晏阳初和梁漱溟分主要从教育入手进行乡村改造。1923年,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会,开展扫盲经典“千字课”。此后不久,18个省、32个市、甚至下辖乡县,也都相继设立平教会分会,识字运动盛极一时。

1929年,儒学大师梁漱溟加入乡村建设运动,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他在农村着力建设乡学、村学和乡村自卫组织。在山东邹平县,研究院派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民种植从国外引进的“托离斯”美棉,组织农民每年在县城举办大规模的农产品博览会,由此,当地棉花成功打入了当时全国纺织业重镇——上海滩。
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给今天的乡村治理与文化重建增添了新的元素。黑龙江五常市二河乡新庄村的村支书刘清泉,今年47岁,担任村支书已经有17年。为了村里发展,他订阅关注了近200个微信公众号,每天一早刷微信,浏览时政新闻和生活资讯,他给每条转发的信息写上自己的政策解读。
【视频】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赋权”
建党95周年,《东方早报》推出11个整版“再访中国村支书”特别报道,讲述中国农村的现状,从农民和土地的不同关系中,寻找中国农村的创新发展。这些中国最基层干部带领村民开发家园,各自走出了不同特色的致富道路。
“让村民办事有去处”的伍志航、“茶园经济写出环保好文章”的钱卫国、“引资近亿建美丽乡村”的黄业平,他们都把互联网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念,植入进了一方水土的乡村治理,成为名副其实的“村红”。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技术究竟如何助力新农村建设?陈楚洁教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所谓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赋权”,这个权力不一定是政治权力,可以是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权力结构的分配,会由某种新技术的介入产生变化。当人有了新的渠道向外界表达、推销自己,是赋权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互联网时代给了乡村很多新的发展机遇,让乡民拥有更多机会,行使自己生存发展的权力。
如今的乡村网红在新农村建设中,有一定的作用,但仍然需要更多观察、期待他们持续见证他们的行动了,发挥其作用。比方说农村产品销售,已经实现了很大的增长,对于带动农民致富,肯定有它很明显的效果。如果我们回头去看以前民国时候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同时需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力量的结合。”
那么通过怎样的路径,乡村网红才能发挥其作用,实现其目标?陈楚洁认为,基层政府、官员、大学生村官,他们如果充分地用新媒体技术来介入乡村治理的话,可以利用他们在体制内的地位,去充分打通、沟通乡村农民的意愿,探索、创新政府的议程设置,进而实现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乃至社会的和谐。
“比如行动路径有,乡村网红可以借助某一事件或者某些场合,做视频直播。今年6月7日,山东省栖霞市西城镇党委书记徐海勇在‘哈你直播’开通直播,为‘栖霞市首届大樱桃电商节’做宣传,同时卖樱桃,效果出奇,当天就卖出了几百个订单。再有,在今年6•23盐城阜宁龙卷风特大灾害中,村淘合伙人组织了当地的村红,大家组成了一个车队,向受灾地方运送一些物资,然后又去当志愿者,他要做社会责任企业,他有营销的一个目的所在,但是也是间接地促进了乡村的治理。”

(编辑:孙燕)
推荐视频

剑网行动举报电话:12318(市文化执法总队)、021-64334547(市版权局)
Copyright © 2016 Kankanews.co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看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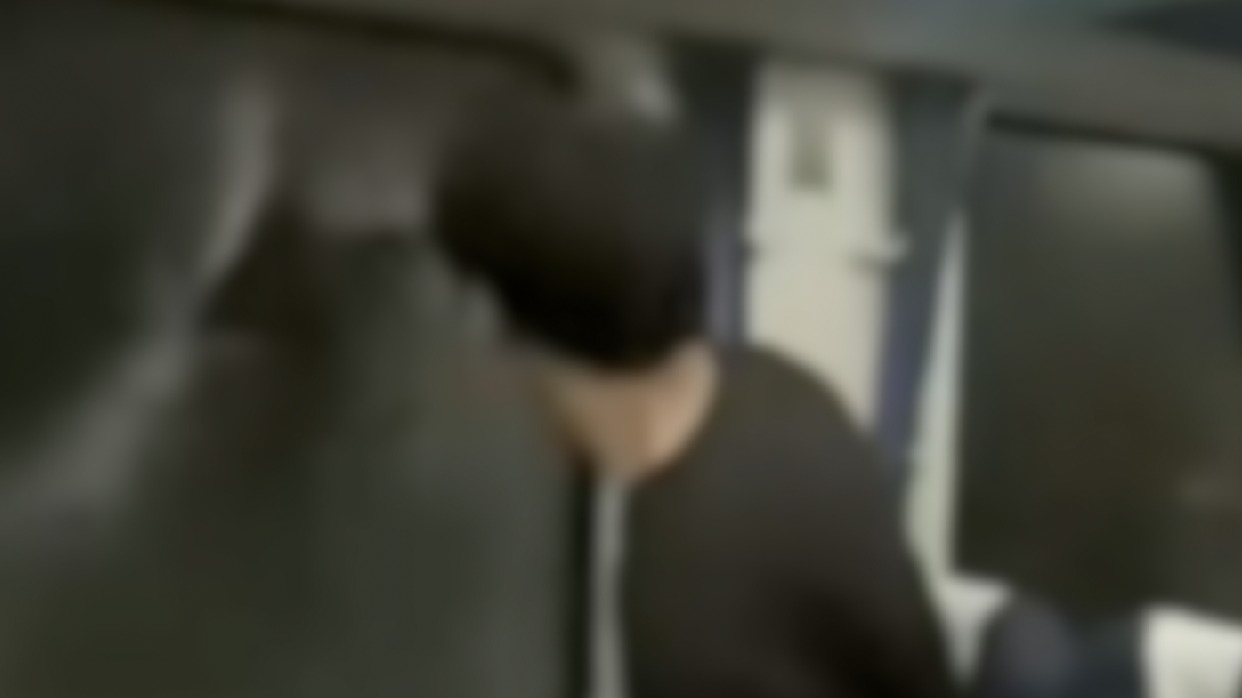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11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114号
全部评论
暂无评论,快来发表你的评论吧